我姥姥家位于山西省灵石县两渡镇张村,虽然我们都在两渡,但我家住的崔家沟,和姥姥家的张村还是有一点儿距离,特别是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,更感觉回一趟姥姥家不容易,倍加珍惜快乐时光。
父亲一辆二八大杠“飞鸽”自行车就能载着我们一家五口儿(小妹还未出生)回姥姥家。哥哥姐姐挤坐在大梁上,妈妈抱着我坐在后座,车把上挂着给姥爷姥姥的礼物,妥妥的,父亲欢实地蹬着,一车载满了幸福。途经大家沟、四千米、两渡镇上,穿过一个地下涵洞,沿河骑行一小段儿,上寡妇桥。寡妇桥年代久远,桥面颠簸,母亲下来走一段儿。过了寡妇桥,就算进了张村地界,但进村的路就是一条羊肠小道儿,雨天是泥,晴天是土,父亲左拐右挪地,将稳稳的安全感给了我们。一路辛苦,总算到了姥姥家。
姥姥姥爷家五个儿子,修着五口砖窑,院子里种植着姥姥爱吃的各种果树,软梨、软桃,丰年挂果的时期,没少进我的小肚子,其余的枣树、苹果树、葡萄树,丰果的年月可能是我们家已经到了古交的事,我没有捞着吃。姥姥家没有像样的院墙,过了石头砌的一道石头坝和小道,就是别人家的公田,那些年净种些蓖麻,惹得我少不了在蓖麻地里玩儿,摘了的叶子当伞玩儿,采了蓖麻,开个小口夹在眼睛上玩儿。姥姥总吓唬我,村上的人发现了要抓起来的。所以对这样的破坏生产的行为,我总是小心翼翼。姥姥家院子南头挖了一个简易的茅房,茅房旁边种植的一株葫芦,姥姥总是不让我去看,姥姥说葫芦害羞,看多了长不大。对于姥姥这个说法,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,那么可爱的小物件儿都,看多了,我如果不摘,也是奇怪了。姥姥家院子北面有个猪圈,吃完饭,姥姥将面汤、刷锅水,里面儿加野菜、玉茭面儿搓成猪食喂猪,姥姥过去用瓢一敲猪食槽,两个二师兄就欢实的奔过来,“哈哧,哈哧……”,欢实的不得了,对两个二师兄充满了“肉”的感情,画面深刻,以至于我到现在见了美食都不敢说“好吃好吃!”只能心里默念着“好吃,好吃!”生怕一不小心露怯。
母亲嫌我们太害了,吃过饭,我们兄妹三人,只能依次放在姥姥家一个,不过也有特殊的一两次,我们兄妹仨可劲的在姥姥家折腾。哥哥长我五岁,我记事儿起,哥哥已经进入了“野”的状态,在工村里是抓不着他的。哥哥的世界,在于广阔的河边、田野、山林和镇上,如英雄般的存在的哥哥,极少带着我玩儿,仅有一次,哥哥来到姥姥家,失去了他的高、大、上的玩伴,只能带着姐姐、表哥、我和表弟一起“作战”了。哥哥给我们一人配发了一支玉米杆儿“步枪”,在院子里整治队伍来回踱步,队伍集结成功,进入“战斗”,玩了一会儿,“八路军条件艰苦,哪有鞋穿,脱了,脱了!”哥哥让我们脱了鞋,继续“战斗”。一会儿,和小姑娘一样的小表弟哭了,我们以大人们的训斥结束了“战斗”,不过也算是我填补了童年的我和英雄的哥哥一道并肩“作战”的空白。
早晨雾气还没散去,姥爷放鸡时,坐在鸡窝边儿一个、一个,挨个儿摸着母鸡屁股,估摸着今天能有几颗鸡蛋入筐。姥爷说这些傻鸡有时也会下些野蛋,沟对过儿的谷场麦秸堆里就有鸡下的野蛋。还有这样的好事?瞅着没人的时候,我就跑到沟对过谷场麦秸堆里使劲儿地翻腾,也没有找着一颗鸡蛋,倒是在麦秸垛里也很有意思。从高的麦秸垛向低的的麦秸垛跳,来来回回的折腾,“谁家小孩儿?”总是以村人们的训斥结束游戏。
姥姥家的后山有个什鸡沟,姥爷在旁边儿开了一片自留地,我感觉什鸡沟就是我童年的一块乐土。
下午姥爷上地时,我就跟姥爷一道到地里玩儿。在地里摘野花儿,在地里逮蚂蚱,什鸡下了蛋也会“咕咕……”,叫个不停,胆小的野兔在草堆里蹦来跳去,口渴了我就喝姥爷地旁的泉水,甘甜算不上,但一定清冽。
沿着山沟向上,随着天气的干燥程度,会发现一条小溪的影子,小溪流着,流着就隐没在了山野。水可能是孩子们快乐的源泉。一个人的筑坝工程也是够忙的,挖土固坝,管了这儿,漏了那儿,忙个不停。玩儿累了,爬上旁边儿的石头山,挖“宝石”,各种颜色的石头,美不胜收。
夕阳西下,回家的路上,在什鸡沟口的葛针树、酸枣树上逮个刀螂玩儿,捏着刀螂的后脖颈,看那个张牙舞爪的家伙左右砍大刀,就是奈何不了我,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。回家喂了大母鸡,明天就是我碗里香喷喷的鸡蛋。
一到晚上,姥姥家15瓦的灯泡,营造了一个昏黄的世界。折腾了一天,想起了妈妈,早早钻进被窝儿,悄悄的流泪。姥姥就过来哄我,“明天天一亮,就让你四舅送你回家。”
第二天,被叽喳的鸟雀唤醒,姥姥忙活着早饭,锅里熬着米汤,满窑洞氤氲一片,我又满血复活,开始了一天尽情折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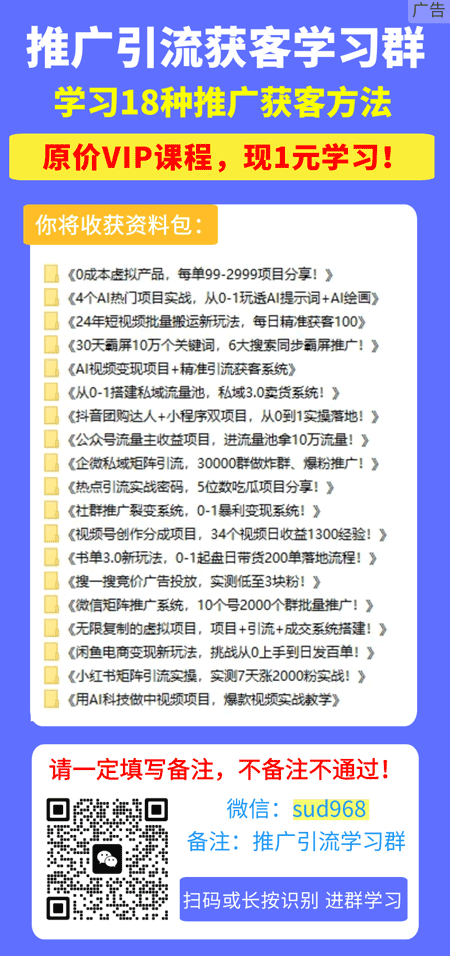
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sumedu.com/faq/71788.html

